《爱俪园梦影录》,李恩绩著,三联书店1984年5月版
即使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文化的学者来说,李恩绩也不是一个热闹的名字。他存留于世的文字,仅有《爱俪园――海上的迷宫》和《爱俪园梦影录》两组文章,合起来也不过一本简简单单15万字的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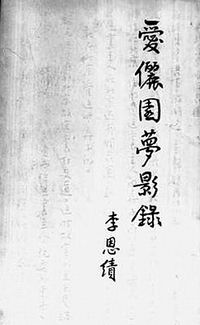
柯老和李恩绩,相识在1943年夏天。彼时正是上海沦陷期间,柯灵刚刚接编《万象》杂志,于堆积如山的废稿中,看中了李恩绩迂阔的“阳春白雪”文字背后的宽广腹笥。于是柯灵一面讲明退稿缘由,一面建议这位来自“静安寺路爱俪园”的作者,写写熟悉的爱俪园。后来,就有了在《万象》上连载的有关爱俪园的长篇掌故。
爱俪园就是哈同花园,英籍犹太人欧司爱哈同的私产。关于哈同和这个园子的著作资料并非没有,但是爱俪园,这个被朱漆大门沉沉锁住的风光旖旎、充满诡奇和神秘色彩的近代“大观园”,却仍被世人的想象和扑朔迷离的传说所笼罩。而李恩绩是最有这个资格谈论园子风物与历史的人,他的朴茂文字可以作信史来读。
光绪三十三年(1907),李恩绩出生。14岁的时候,他跟随在爱俪园作画师的父亲进园学画就读。他曾在园中的仓圣明智大学就学,以后在园中的主要工作是为文海阁编藏书目录。这些工作给了他研读古籍的机会。他在园中多是写字作画,发挥其书画、词章和古文字学养。所以,李恩绩笔下,除了描述园中景物、人物和故事之外,也关注其中的文化学术掌故。李恩绩写景多关注碑帖题跋绘画,有多处关于园中举办学校的描述,以及文明书局、彪蒙书局与爱俪园的交往。
“迷宫”和“梦影录”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叙述,是关于王国维与爱俪园。这足可以丰富后人对于静安先生的了解。
大管家姬觉弥在园子里开办仓圣明智大学和女学,还有广仓学?、广仓学文会、广仓学古物陈列会等,并印刷《广仓学会杂志》。广仓学?的主要成员就包括当时已为学界所熟知的王静安先生。今日所见王国维与爱俪园关系的文字,只有见于《王国维遗书》中的一些简单句章。例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中说,“得见英伦哈同氏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拓本凡八百纸”(《观堂集林》卷九)。事实上,王国维在爱俪园中留下的印迹远不止此。他在这里编《学术丛编》,后分成二集,更名为《广仓学?丛书甲类》。姬觉弥发现丛编工作非王先生不可,就干脆放弃校勘权,全部委托给他。广仓学?的另一位主要成员邹景叔编成《艺术丛编》,后来改名为《广仓学?丛书乙类》。其中一篇《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书题“睢宁姬佛陀类次”。但是李恩绩说,“其实这类次的工作,还是王静安先生做的。”包括《重辑仓颉篇》和《唐写本唐韵残卷校勘记》等,都是在园中时代替姬觉弥所编(第277页),后来这些文章的自序收入了“遗书”(《观堂别集》卷四)。
更可爱的描述在于李恩绩笔下“王静安先生的一些佚事”。我们一般多是从几张常见照片中获得静安先生外貌印象的,这里请看李恩绩的描述:
一个不很高大的身材,面孔也瘦小,牙齿有点獠在外面。常穿着当时通行的及法布袍子,罗缎短袖马褂。后面拖了一条短辫子。冬天他戴上一个瓜皮帽子,或者穿上羊皮袍子。但他没有比羊皮更高贵的皮衣。他的衣式不很时式,也不很古板,但很整洁。他的近视眼镜是新式的。他也会抽香烟。总之他的物质生活,是很随随便便,决没有一点遗老或者名流的气味。看去有点像旧式商店里的小伙计。
静安先生的为人:
他对人不很会讲应酬话,更不会客气。假使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假使说是“靠不住的”,那个人无论找出一些这样真实证据的话来,例如色泽的如何古雅,青绿的如何莹澈,文字的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著录。将这些话提供给他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是“靠不住的”四个字答复,也不附和人,也不和人驳难。
有时姬觉弥要和他解决一个字义,他只嘻嘻的一笑,或者有机会更跑远一点。我想他是感到和这位“小学大师”学问的途径有点不同,所以不肯多非难,引起无聊的误会。
静安先生做学问的风格:
他家里旁的东西都不多,书也不很多。不过他的书不是整整齐齐堆在书架上,却是到处摊着。桌子的每一只角里,茶几上,椅子上,床上,甚至于地上,都摊着翻开的书。要等他把正在起草的一篇著作告竣了,才把摊着的书整理一下。到第二篇著作将要动笔之前,书又随处摊满了!(第274页)
爱俪园所藏甲骨,对于静安先生的古文字研究,确实起到了不小作用。李恩绩在这方面是有发言权的,因为他对甲骨文字也有深厚的修养,能够指出王先生甲骨考释的错误(第186页)。他说:“在戬寿堂购进的甲骨中,却依然有许多有价值的文字,后来被王先生发现出来。其中有‘中宗祖乙’,‘小祖乙’等字的,在刘[铁云]罗[叔言]所印的书中,都不曾有过。”(第178页)
但是,静安先生在爱俪园仓圣明智两校的教学却是失败的:
这时王静安先生已从东洋回来……在尚未开始编书之前,还请他在学校里上课。当时在光复之后,年轻的人,总得学个时髦。学堂里的学生,对于这位拖着小辫子的王先生,不大欢迎。还有一层,王先生虽然懂得教育学,但实施起来,因为他不会高谈阔论,做不出噱头来,引不起学生的兴趣。(第59页)
这几段描述使后人得以因此对王国维多一些了解,但是王国维的光芒遮蔽了他的描述者,很少有人去追问这些文字的源头。
李恩绩具有旧学根底、学者眼光,又兼史家素养、文人情趣,温和幽默的文字往往令人捧腹。比如他讲仓圣明智大学的郑琴师。这位琴师技法一般却颇喜讲琴理,李恩绩说他虽然是极普通的琴理,“出于郑琴师之口,入于姬觉弥之耳,似乎比康德从‘实理批判’发展到‘纯理批判’,还奥妙十倍。”(第287页)
园中还有一位绰号“大藏经”的绍兴师爷,单是李恩绩??嗦嗦解释这外号的来历,就够人笑痛肚皮。“大藏经”喜欢吹牛,常把《洗冤录》上的事情,说成是自己经办的案件,还自吹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皆在腹中。但是大家却记得他做过一首没有成篇的祝寿诗,“他这首诗虽然仅仅做了一联,却还有人传诵。因为罗迦陵是七月初七生日,他这一联诗正是描写七夕的景致。他这一联诗句是:‘天上鹊桥银汉白,人间马路电灯红。’”而诗句没有完篇的原因,是“他的同事们未免少见多怪,听到‘马路电灯红’,不觉哄堂大笑。于是他的诗兴再鼓不起来了,所以没有完篇。”(第298页)
这样的学养,这样的文章,李恩绩托付给柯灵先生,真是找对了人。
柯灵和李恩绩的相交相托,和李恩绩笔下的爱俪园文字一样,如今都成了令人感慨唏嘘的掌故。当年,柯灵为了让李恩绩继续写《爱俪园――海上的迷宫》,亲自找寻作者,“我观光爱俪园,和李恩绩见面,这是生平难得的一次”(第3页);六七年后,柯灵忽然收到李恩绩从绍兴寄来的《爱俪园梦影录》手稿。这些未经人道、历历如绘的姊妹篇章,在时移世易、建国初肇之际,自是不合时宜。所以,这些难谋出路的文章不免沦落成尘。此间,编辑作者两相茫然,断了音讯。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柯灵在责任心的驱使下,为“梦影录”寻找出路,并再次辗转打听作者,这才约略知道了李恩绩的生平。这次,柯灵没有见到作者。
原来,生性疏阔的李恩绩在抗战胜利后,回到故乡绍兴。全国欢庆解放的年月,却是他个人“每餐吃粥,有时一天还只吃两餐”的“饥饿时代”(第186页)。就在这偃蹇困居中,他整理校勘了历年积存的甲骨文拓本和摹本共400余张,“用粥液代替浆糊,依次粘贴装订成册,寄给了郭沫若”(第6页),但没有得到回音。也大约在此期间,他完成了《爱俪园梦影录》。李恩绩无子无女,只有一位半文盲的老伴,二人靠卖书画和摆香烟摊糊口。他把“梦影录”寄给柯灵后,从此不闻不问。“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甲骨文原件、拓本和著作,统统落入“造反派”手中,下落全无。而他本人,也在抄家和揪斗中默默死去。
柯灵老慧眼,为我们保留了这样才华出众、学养深厚的文章,虽然他没有能力让这文化的书写者拥有一个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这不是编辑的责任。如今,我们面对李恩绩俊秀儒雅的手稿笔迹,一边可怜可惜,一边恨不得责备文化之脆弱。苍天不佑李恩绩,痛煞后人。
(本文编辑:李焱)
